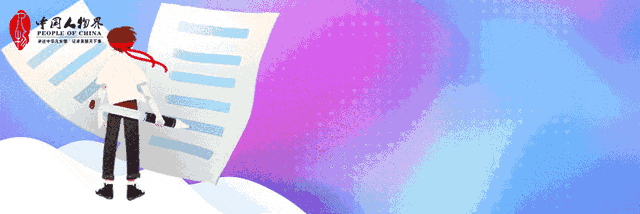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周嘉宁说,“《浪的景观》是我会写进简历里的作品”。也许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周嘉宁就和文字签订了一份契约,让她能够建造出虚构的空间,使人物在其中安顿、游荡并寻找着出口。《基本美》之后,新书《浪的景观》再度回返那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在记忆中打捞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状况。
我们跟随着人物漫游在真实与虚构双重叠印的版图中,上海、北京、台北……和他们一起站在交替的路口,想象那个盛大的未来在每一个人心中激荡起的震颤。当青春的开场过于盛大,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走向失望与虚无?

《浪的景观》,周嘉宁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浪的景观》向我们指证着,对虚幻的醒觉并不直接走向自我否定。即使有关进步的浪潮终将散去,即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那些已成记忆的欲望、情感与感觉,仍留存于我们的身体里,作为我们与时代发生摩擦的见证。
周嘉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感觉——历史并非完全指向宏大,而是对个体生活世界的无限挖掘,而对于一个作家,重要的不是描述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经过了一代人,而是去捕捉浪潮之中,每一个人的兴奋、紧张、游移、观望,这些千差万别的反应构成了历史的鲜活——“这几年里,我只是花了很多时间记录和描写各种形态的浪,水的阴影与分界线”。
《浪的景观》结尾,主人公见证了一场骗局,转身说,“我的朋友在等我”。
也许,周嘉宁想告诉我们,梦醒之后并非无路可走。也许,当我们去往彼时彼刻,体验时代与青春之间的共振时,会想起那句——“人类还年轻,人类要活下去”。

周嘉宁,作家,英语文学翻译。出版有小说集《基本美》,长篇小说《密林中》《荒芜城》等。
“我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者,
而不是一个引领者”
新京报:你之前在播客里说你一直喜欢北京,之前在北京住了多久?
周嘉宁:之前住了三年,但那时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我对北京一直有感情,现在也没变过。2010年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离开,包括为什么周围很多人都会离开北京。但今年这个时间点,我会永远记得今年发生的事情,即使过去很多年。我最近在做一些采访,也涉及城市的变革。我采访了一些爵士乐相关的人,他们提到大概从2002、2003年开始,有很多外国人来北京,把爵士文化在北京、上海传播开来,爵士演奏的酒吧也出现了。到2010年就出现了低谷,在上海的外国人几乎都离开了,一下子出现了断档,我觉得还蛮巧合的。
但我具体说不上那两年发生了什么,无非是2008年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整个城市有很多基础建设项目都在为之做准备,上海大批居民区动迁,都变成了世博场所。以前我住过的一些地方全拆掉了,我很喜欢的那些泡桐树也被砍掉,都是为世博会做准备。2001年到2010年是建设的时期,通过这10年的建设,基本上就决定了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城市的基本面貌。
那时想离开北京,不是因为我对北京有什么不满,而是上海在世博会之后出现过一段非常短暂的,用当时的话讲,很短暂的“文艺复兴”。当时,上海出现了一些很小的、民间的文化现场。静安区有个地方叫“静安别墅”,我一些朋友在那里开了一个图书馆,用波拉尼奥的《2666》命名。那一年,静安别墅里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地方,都是违章的,没有经营执照。当时上海书展邀请了很多国外的作家,他们同时会去“2666图书馆”做小型活动。可能就是那两年,我突然对上海产生了一种渴望,我想到现场看看,我想参与。
新京报:你刚刚说,你从北京回到上海,是因为对那些突然产生的、民间现场产生兴趣,你一直有这种想去参与的热情吗?
周嘉宁:对,我从小就对很多现象好奇。也不是要参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善于参与到社群里的人,但我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引领者,或者我可能不会甚至从来不会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新京报:这种热情是否和你选择做记者有关?
周嘉宁:我其实也没有选择做记者,最开始是为了赚钱。我高中的时候就在做记者的事情,因为喜欢写作,但当时并没有成为作家的概念。我觉得我喜欢写作,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因为记者要写东西。所以我高中时在上海的《青年报》做学生记者,认识了很多人。我大学那几年的记者经历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整个媒体行业非常有趣。
2001年,上海的《东方早报》刚刚创立,每周五有一个100页的特刊。特刊部的人非常有趣,我当时在周报部门实习,周报跟特刊部同属一个报业集团,我在他们楼上。我和他们同样的时间上下班、吃午饭。遇到他们的时候,明显感到他们的人比我们的人要有趣。我很想加入他们,他们也不需要打卡上班,随时通宵,感觉办公室一直有人,做的选题又非常有趣。后来,我也会帮他们做一些城市观察的稿子,那时候上海在做很多大型的城市建设,所以会跟他们的记者一起跑一些地方。对我来说,那段经历很有趣,因为自己正好处在一个对外部特别感兴趣的年纪,你会对整个城市中那些庞大的东西好奇——大型的工地、烂尾楼,当你进入这些楼内部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身体感受。
新京报:我很喜欢《浪的景观》这篇同名小说,结尾处写到“我”被骗到海边参加一个所谓“魔岩三杰”的演唱会,但仍旧有力量说出:“我的朋友在等我”。这是你区别于很多书写世纪之交作家的地方,你回过头来拥抱了自己的同时代人们。你怎么理解,以及这里有一种对虚无的抵抗吗?
周嘉宁:我跟吴琦聊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说法——“青春开场得太过盛大”,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是有影响的,但可能因为我本质上比较乐观,觉得还没到虚无的时候。难道你觉得此刻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好像也不是。我其实并没有那种,认为上一个时代是黄金时代的想法,完全没有。
我最近在写新的小说,我想起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以前住的地方,我念书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随着城市的建设,没有外在媒介来帮助你进行回忆,而且我经常会路过那些被重建的地方,可能造了很大的商场,或者城市绿地,去那些地方的次数越多,记忆被覆盖得越来越确定。因为眼前的场景是确定无疑的,它对记忆的覆盖非常严重,我不确定自己对以前的记忆是否准确真实,可能只留下来一些感受,但感受这个东西也是被自己修正过的。于是,你无数次重新思考和讲述的经历,都是通过被修正的东西。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中,青春、夏天、年轻人成为了一种关键词,这种“少年感”似乎和你所注目的2000-2010年时代的上升之间互为表里。在逐渐走向一个下沉的年代时,这种少年感还存在吗?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周嘉宁:好像是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不太清楚,也跟自己看待人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比如,你有一个从小认识的朋友,即使过了很多年,这个人的生活可能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他的性格中也有很多你不适应的东西,但原来你熟悉的那些部分也没有彻底消失。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并存,人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会有多面性,他有可能在不同的社会面、或者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出不同的东西。
人的性格当中有那些忽隐忽现或者忽闪忽灭的部分,会在一个波动中,这不是恒定的。所以,我不觉得存在所谓“被社会彻底改造”,人的某些面向在某个时期可能会占据上峰,但也不代表他永远就是这样。
大的事件辐射到个体所产生的能量是不同的
新京报:你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想象历史的方式,当外部世界已经被完全改造,不再为我们提供物质上的通往过去的通道时,那些仍旧留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心情、感觉反而成为我们去回忆时代的一个通道。我之前看很多书写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总在强调人在快速变化时代面前的被动反应,人在浪潮中似乎总是无力的、失落的、被动的,但我在《浪的景观》里看到了人并未被摧毁或折损的部分——那些实实在在的欲望、激情和情感,这个很有意思。
周嘉宁:所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人未必会有及时的反应,发生之时可能会被震撼到,但又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一开始波及自己。凡是大的事件,它产生的影响、余震,有时会缓缓地释放出来,而非在当时立刻浮现。
我会选择的叙事角度,是从个人的、具体的境遇出发,而不是从一个更大的范畴辐射到个体。我想从个体的角度去感受那一段的历史,而且关键在于,一段历史最终辐射到每一个人所产生的能量是不同的。同样的历史事件对人命运的改写是不一样的,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也未必会让一代人全部消沉,或者说会让一代人都积极乐观,这是不可能的。
你要去把握,这个人的自身能量跟这些宏大的浪潮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互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互换的过程。
新京报:所以可以说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是你创作的核心框架吗?
周嘉宁:对我而言,日常生活还好,我不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人,或者觉得日常生活一定要过好。但我在乎单个的人、独立存在的人,并尊重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差异。庞大的东西会抹杀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会强调同一,仿佛你在一个浪潮当中只能看到那些被席卷而过的、被动反应的人,他们被书写成了一个整体。但是我觉得,即便在大时代中,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你不能够忽视这些差异,即便很微弱,这个东西也很重要。讨论这些会让我觉得有意思,也会消解一下庞大的东西。我们时代当中有很多庞大的东西,要去消解一下,要看到各式各样的差异。
新京报:从小说集《基本美》到《浪的景观》,能看到你的写作视点从单点的“我”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转向多角色。这种作品声部的转化是否和你近几年生命经验的转变有关? 从《基本美》到《浪的景观》在创作和命题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周嘉宁:人更年轻的时候,都会经历希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纳的过程,害怕误解,想要说清自己的观点,尽量被更广大的世界接受。我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想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后来觉得自己的观点也越来越复杂,变得好像不能用“表达”这种形式去呈现,我需要别的形式,甚至未必需要表达。
所谓被理解和被接纳也不再重要,我接受所有误解,全都接受。一旦这样之后,自由感就强烈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存在了,如果作为作者的我都不存在了,这个小说是谁的小说?我为我的主人公搭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肯定不是现实的世界,小说世界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而每一个创作者和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通道进入它。
在虚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作者亲自制作出来的,我使用工具去创造它,让我的主人公可以有容身之处,替他们扩展一下疆域,让他们有更多地方可以探索。但我未必要和他们对话,我也未必要把我的想法灌输给他们,我希望他们在虚构世界里拥有自由。我希望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创造者、建设者,也不仅是旁观,我在建造、在替他们做一些工作,有时提供一些保护,不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被摧毁。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两个世界,但虚构世界并非孤立于现实,那么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实要经过怎样的转换才能被安放到虚构世界中?
周嘉宁:我是个充分参与现实世界的人,会对很多事情感兴趣,愿意看到各种各样的讨论,即使是有冲突的观点,我也会愿意去思考。我希望现实世界跟自己是有碰撞的,而不是在一个比较顺滑的状态中。如果个体同世界的关系是比较顺滑、没有摩擦的话,很难产生出虚构的世界。
虚构的世界是个人的能量与现实世界的碰撞中所震动出来的产物。这种碰撞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它也不是每一次都一样。现实世界同创作者的每一次碰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有的时候是摧毁性的,有的时候是建设性的。
它跟现实世界有互相映照的过程,或者说有震动的频率,有时它们偶尔重叠一下,但绝对是两个世界。但如果虚构世界是彻底独立的话,读者就没法进入,只有它跟现实世界之间有无数个通道,读者才可以自由地出入。
虚构世界跟现实世界是一个大的映衬关系,首先他们肯定不是互相模拟、模仿,谁都不是在模仿谁。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其实也说不好,我觉得不要有这么明确的定义,但我相信,但凡进入过虚构世界的人,其实都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是你进入过你就知道虚构世界的存在,你也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的,但它们到底以什么样的关系融合在一起,这取决于各种情境和当时你自己所身处的情况。
不能否认我这一代人的幸运
新京报:你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流行音乐,比如王菲、谢霆锋、窦唯、罗大佑等等,音乐对你的小说意味着什么?在2018年的采访中,你说还没有找到让音乐与小说共振的方式,现在找到了吗?
周嘉宁:我没有找到,当时可能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感觉,现在越发确定了,还没找到。我确实期待,音乐可以搭建一种平台,暂时消解大家的分歧、误解与偏见。其实不仅音乐,艺术、文学从某种方面说都承担着这样的作用,大家很多观点完全不一样,但至少还可以保留一个平台,保留一个可以对话的方式。
新京报:新世纪初十年似乎还能找到很多流行于整个世代的音乐,但我们现在似乎很难找到可以共享的声音,随着大众文化逐渐垂直、分众,如果你要去把握这十年的时代氛围,你会选择音乐吗?
周嘉宁:老实说很难,因为一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在听什么。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不听了,还是因为真的没有时代金曲了,我也不好下定论。总体来说,我觉得青年群体是一个会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的群体,他们会很自然地形成自己的堡垒,有排斥性的,也是一个比较“残酷”的群体。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我就想,我会不会很积极地把我喜欢的东西介绍给比我年长、或者跟我不一样的人?而且,如果要讨论青年文化,应该是青年人自己去写或者明白要怎么样去讨论。
与此同时,当下青年人所喜欢的东西,还包括生活状态,有时让我很难用文学或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其他的媒介反倒更有力。所以,我在想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因为20年前的青年生活,它是以文字为媒介的,所有人是用文字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也是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之后你再去书写这个时代,自然而然是使用文字。但现在你要如何记录大家的表述?大家日常对于自己生活的描述,不管是网红也好,各个领域的KOL(意见领袖)也好,他们是此刻最把握时代脉搏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己的描述、传达方式不是文字的,你要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文学的形式,很奇怪。他们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文学的方式存在,甚至不是以文字的方式存在,我在琢磨这个东西是否一定要变成文学的方式去传递?
新京报:继续聊聊年轻人,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假装活在1980-2000年”,小组成员大多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要怎么理解这些年轻人的“怀旧”?可以参照的是, “Y2K”这几年也重新成为流行,该怎么理解这种大众文化空间中对世纪之交年代的怀旧?当下的怀旧真的是想要回到过去吗?还是说,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时代所想象的未来——一个已成过去的未来?
周嘉宁:只能说明时间到了,因为你现在距离上世纪90年代已经过去快30年了,这个时间量足够你进行怀旧了。所有的时代潮流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在一个轮回里,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大家也都会去怀旧七十年代(不一定是内地的)。这种东西只能说明30年、或者25年是个圈,之前被抛弃的潮流时尚突然又可以回来了,但是它一定是经过变形。我现在也会刷到类似于2000年的街拍,但现在你真的还能够打扮成那个样子吗?肯定是不行的。它只是有一些元素拿出来,重新经过时代的改造,又变成一种并非完全复古,而是要经过改造的,不然难道现在还可以再去使用诺基亚手机?大家现在其实也只是拿着智能手机,在更为现代化的方式之下去完成一些时代想象。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周嘉宁:以前没想过,现在总有人说我很幸运,或者说我们这代人幸运,我刚开始时还会反问,你说的幸运是什么?但后来确实觉得,不能否认这一点,时代给予过的馈赠,别不承认,认为这一切全都凭个人的努力。这当中一定有一些机缘巧合,一定也有好运相助。
(采写/吴俊燊)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