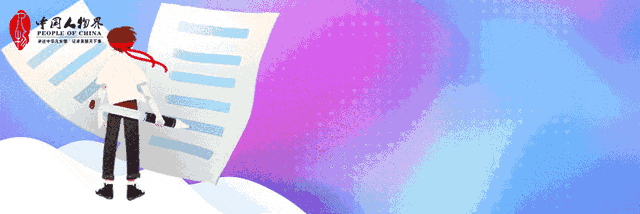梁晓声:文学是人生的底色(名家近况)
这几个月,小说《人世间》俨然成了梁晓声生活的“主题”。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收割”了老中青几代观众,把这部本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和作家本人又一次推向了前台。他感激大家对作品的认可,也因纷至沓来的采访和活动而感到有点累。采访前,梁晓声有言在先:“《人世间》谈得很多了,就不再谈了,希望大家读一读我的新小说《中文桃李》。”
实际上,自2017年底《人世间》出版后,梁晓声一直保持着高产的写作状态,先后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一部是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桃李》,都聚焦于“80后”青年的成长,以年轻人视角写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之歌”。尤其是新作《中文桃李》,被梁晓声视为自己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小说。他说:“写作跟面点老师傅开面馆没多大区别,我还有一本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写完后,不管水平怎么样,梁记面食店就要关张了。我的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不能浪费。”
写给中文系“80后”
2002年,梁晓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与青年学子有了直接而频繁的接触。当时,他的学生正是“80后”一代。多年来,他关注着学生们离开校园后的人生际遇,想通过小说的方式,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也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曾经教过的学生。
《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世纪之交,李晓东考入本省文理大学中文系后发生的故事。他和同班男生一起听汪尔森教授的课,获得文学启蒙;办《文理》杂志风光一时,刊发的作品被《读者》转载;接触有点各色的女生徐冉,初尝爱情的纠结与甜蜜;面临升学和就业的压力,探寻前路何方……在这所大学,以李晓东和徐冉为代表的青年学子,在经历同学间的矛盾、冲突与误解,经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考验后,收获了成长、友谊和爱情。他们带着中文教育的四年所得,步入了小说下半场。
《中文桃李》是一部写给中文系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文可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专业,才子和才女们都在中文系。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梁晓声说:“后来文学开始边缘化了,当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学中文时,中文系好像成了一个‘筐’——过去是喜欢中文才去读,现在可能是权宜之计,出于理科成绩不理想才无奈去读。”但在他看来,学生在中文系收获的人文教育,尽管不会令他们短时间内获得财富和成功,却培养了他们的从业能力、读书能力。比如小说中的李晓东,因担任《文理》主编,在日后省电视台、出版社、广告公司、房地产公司、纪录片团队几份工作中,每每能做出不错的成绩,以至于多年后妻子徐冉对儿子说,“你爸的人生,现在仍靠文学那碗饭垫底儿”。
和《人世间》相比,《中文桃李》给人的感觉没有那么多忧患与沉重。书中不乏一些“小幽默”和贴近年轻一代的网络语,如“公式(音duǐ,指顶撞)”“佛系”“颜值”等。“写年轻一代对我是个挑战,首先是语言不一样,尤其是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因此我在语言上尽量融入年轻人。”梁晓声说,“代沟肯定是有的。到年轻人中去,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代沟还在。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我们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如果说同代人写同代人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梁晓声写“80后”,则多了一些“审美距离”。“‘70末’‘80后’作家写同代人或多或少有顽主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我觉得这有点标签化。我接触的学生不是这样。我更喜欢自己笔下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没有顽主的感觉。”
过一种“报告文学式”人生
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永远是困扰年轻人的问题。《中文桃李》中,女主人公徐冉问李晓东:“生活也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小说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你憧憬哪一类生活?”两人商量一番,觉得没谁的生活可以始终如歌,史诗类的离普通人又太远,诗类的太理想主义、太脱离现实,小说类太难把控、太复杂,而散文类的更适合老年人,还是报告文学类更恰当——人生像一场自己给自己的报告,由不得虚构、自欺欺人,而又得有点文学性,加进小说、散文、诗歌的味道。
这种以文学门类来比喻生活的做法,是梁晓声的创造。他说:“这是过来人的看法。我没经历过诗一样的人生,压根就没敢那么想过。从少年时期我就笃定,这辈子得像报告文学一样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伪——因为家里困难。”
小说下半场,两位主人公毕业进入社会后,也确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心中保有着对对方的“责任意识”,认真地为生活打拼着。他们住过简陋的平房、昏暗的地下室,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逢,最终过上了如意的生活。而李晓东和徐冉也终于取得家长的认可,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
纵观这两个人物走过的道路,确实代表着很多“80后”青年的心路历程。他们纠结过,是留在家乡陪伴父母,还是远走他乡到大城市闯一闯;他们面临户口、房租、工资等生存压力,却不甘心做有违本性的工作;他们不愿“啃老”,以占朋友的便宜为耻;面对不可回避的代际冲突,他们逃避过、争吵过,最终理解了父母、收获了亲情。《中文桃李》堪称是“80后”青年一代的心灵史,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写出了这代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对待情感的态度。
在梁晓声看来,小说家眼里不能只有小说,小说应该回应各种社会问题。他把作家定义为时代的记录员,认为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既是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关心他者的命运。
《中文桃李》触及的一个社会热点话题是:年轻人是否要留在北上广深。作家把李晓东、徐冉这类“北漂”青年形容为“吊兰”,借主人公之口把北京分为了平时“动车式”的北京和过年时“绿皮车式”的北京。李晓东觉得,前面一种有“北漂”的北京更可爱,但他最终选择回到故乡,加入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纪录片拍摄团队。“小说中设置灵泉、省城和北京三个层次,并不想给出主人公留在哪里是对、哪里是错的结论。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抉择是一种利弊、一种权衡,而无关对错。”梁晓声说。
《中文桃李》延续了梁晓声以往作品对“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的思考,只不过他观察的对象从《人世间》里的“50后”变为了“80后”。但他的答案没有变——“70多年的人生走过,人一生到底该追求什么?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云烟。”
大学需要人文气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中文桃李》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也是一本大学教育之书。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中文系教授汪尔森。他的课妙趣横生,让本想跨专业到对外汉语的学生也被深深吸引;他鼓励学生办刊物,推荐优秀作品发表;他和学生交朋友,让大家毕业多年后还每每怀念……更重要的是,他是学生们名副其实的“精神导师”,引导学生思考人性和人生的意义。
《卖火柴的小女孩》对人类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汪老师说,读过它,同情的种子会在心里发芽。之后再读《快乐王子》《苔丝》《悲惨世界》,“那么,他成为警长的话,也许就不会是沙威;她成女议员的话,也许会特别重视慈善工作,使卖火柴的卖花的无家可归的男孩女孩受到关爱而不再被冻死”。
何谓“深刻”?汪老师说,它好比是瑞士名表里的钻石,“钻石就是发人深省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过目不忘的文字或对话……深刻并不等于危言耸听,也不等于哗众取宠之论,更不等于对人性丑恶险邪的一味展览。”
常言道“文学是人学”,那么“人”是什么?汪老师说,人是欲望的宿主,也是理性之摇篮;人是文化的盛器,也是社会关系之和;人有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人的好奇心催生科学,人的娱乐渴求催生文艺……
其实,汪尔森正是梁晓声的自画像,书中汪老师讲的内容就是学生们挤爆教室也要听的梁氏文学课。“中文系教师只讲如何读懂一篇小说,还远远不够。应该更多地从作品出发,引发学生思考人生。比如我跟学生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和《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有怎样的异曲同工、罗丹的雕塑《人马》给我们理解人性以何启示?这些思想性的话题及其延伸的讨论才是最有价值的。”梁晓声说:“我不认为讲课一定要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似乎不这样就不行,一堂课只有45分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
他还发现,课堂上的男生比较内向,不愿意发言,导致听到的讨论之声都出自同一性别。“这对讨论本身是一种遗憾。我们常说,要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其中就包括性别——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看,这个碰撞是很有意义的。”梁晓声说。
上过梁晓声课的学生都知道,尽管课上讨论的问题严肃,但气氛却是放松和活跃的。他曾带学生看电影《出租车司机》,出资让学生买来饮料、面包、糖果,让大家边吃边趴在桌子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只有老师一个人拿着粉笔在讲台上。“我觉得文学课其实这样讲才对路。”梁晓声说。
在小说中,梁晓声借汪先生之口说出了他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坚守:“文学专业是一个什么专业呢?首先是一个了解人性进而了解自己的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大学之魂。没有点儿人文气氛的大学,不可能是一所好大学……”
他强调人文气氛,其实是一种信念,相信“文学确曾起到过这么一点儿促使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点儿一点儿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响着世道人心”。也正是在这重意义上,文学是人生的一种底色。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