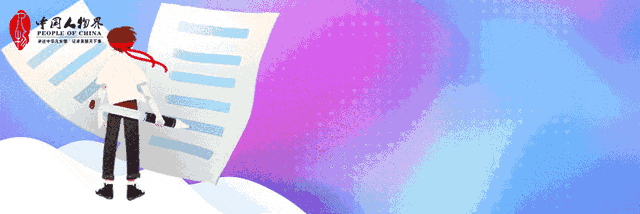误传近千年 一朝迷雾散——陕西江村大墓是这样被确认为汉文帝霸陵的
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所在区位,似乎在历史上早有定论。然而,近千年来被认为是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却并不是这位帝王的真正归宿之所。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后,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选。汉文帝霸陵位置的确认,不仅纠正了讹传之误,也填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
半个世纪的考古接力
早在元代,就有史料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凤凰嘴”位于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凸出的山头,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其山,不起坟”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碑石,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题写的“汉文帝霸陵”石碑也在此处。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汉文帝的霸陵位于“凤凰嘴”。
“文献记载,汉文帝决定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这个记载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里误导了人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但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汉文帝的霸陵所在地。
2011年至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带队对霸陵、南陵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那时,尽管我们已经探明‘凤凰嘴’无任何陵墓遗存,但要直接说江村大墓就是霸陵,证据资料还是不足。”马永嬴说,“直到2019年,我们惊喜地发现,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外围有更大范围的陵园园墙遗存,这说明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同处一个大陵园中。”由于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是“同茔异穴”的葬制,而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同茔”,这成为确认汉文帝霸陵的关键性证据。
至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接力,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完整证据链条已全部呈现:其一,江村大墓有4条墓道,呈“亞”字形,且规模巨大,这在汉代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皇后可以使用;其二,对“凤凰嘴”进行考古勘察后,没有发现墓葬和相关文物,这对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是个强有力的支撑;其三,将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围合在一起的外陵园的发现,表明了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关系符合西汉帝陵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其四,在江村大墓外藏坑发现了诸如“中司空印”“北葆司空”等明器官印,这说明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机构,数量众多的外藏坑围绕江村大墓,它的墓主非皇帝莫属。
“减礼不减制”的薄葬理念
“霸陵真正位置的确认,让田野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工作有了明确的对象,也让人们对于汉文帝的薄葬和节俭,有了新的认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说。
汉文帝刘恒为西汉第三代皇帝、“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他的陵墓霸陵因“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而没有封土,其地望虽在白鹿原,但具体位置却在历史演变中逐渐模糊。“此次江村大墓的发现明确了霸陵不再是以‘因山为陵’而作为西汉帝陵中的一个特例,需要重新审视其在西汉帝陵形制布局发展演变中的地位。”曹龙说。
江村大墓的形制为“亞”字形,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3米,四周环绕115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窦皇后陵现存“覆斗形”封土,墓葬呈“亞”字形,陵侧有10多座外藏坑,周围有夯土园墙和门址。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外围的夯墙遗址,东西残长1200多米,南北860多米,墙宽约3.5米,该墙址就是围合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大陵园墙。在大陵园内外,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外藏坑、建筑(包括陶窑)遗址、陪葬墓等文物遗存。
“汉文帝的薄葬,主要的体现就是‘减礼不减制’。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地势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陵园以石为界,不修筑高大的陵园园墙。但是汉文帝毕竟是一国之君,虽然可以‘减礼’,但是帝王的规制却要充分体现。”曹龙介绍,虽然《史记》和《汉书》等多部古籍都曾经记载了汉文帝的薄葬,但是此次霸陵的确认,让人们对汉文帝的“薄葬”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弥补西汉帝陵演变关键环节
“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汉文帝开启了‘文景之治’,当时是西汉转型的过渡时期,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政治思想都在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帝陵制度上。”马永嬴说,霸陵位置的确定,以及陵园形制的掌握,填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对西汉帝陵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西汉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研究来讲,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的,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的形制布局上承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阳陵、茂陵等陵园规制,是研究、探讨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此外,南陵外藏坑出土了众多带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包括熊、狼、豹子等。这些金银器具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风格,体现了先秦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