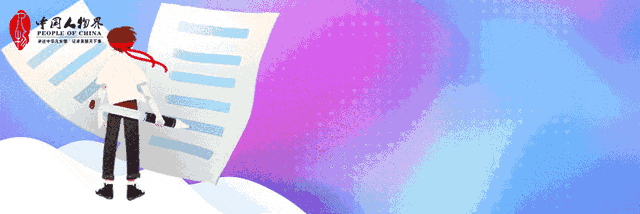长发披肩,一袭樱桃图案、金色纽扣的黑色上衣,配着同样色系的短裙和细高跟短靴,眼前的郝景芳,素雅中透着精灵般的活泼。
身为亚洲首位女性“雨果奖”得主的80后科幻作家,郝景芳没有印象中名人的高冷和距离感,言谈温和,始终面带微笑,那是来自心底的清泉般的喜悦。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作家和教育领域的创业者,干练中依然散发着女大学生的气息。
“我是一个创造者”
郝景芳很忙。
“每天早8点到晚10点,我都在忙各种各样其它的事情。晚上10点家里人都睡了,或者在出差的路上才有时间写作。个别时候,一本小说还差一段收尾了,我会闭关三四天写完。
今年7月我在秦岭闭关。留坝山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空山鸟语。想起楚汉之争时,英雄翻山越岭,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林木与云雾……”
难得的悠闲。
在别人眼里,郝景芳是学霸,是清华大学天体物理硕士、经济学博士;是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是宏观经济学家、世界青年领袖、童行书院创始人,但郝景芳对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创造者”。
“无论是写小说,还是从事教育、做儿童游戏化学习APP的开发,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些我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内心被触动,是写作最核心的动力”
“以前我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从河北一个小城市过来北京打工的。他想让小孩上幼儿园,但附近能接收的幼儿园都特别难上,家长带着铺盖在幼儿园门口排一晚上都可能上不了,他非常发愁。就是这个很小的触发点,让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一个艰难生活的父亲想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心情特别打动我,要把这个人物写下来。于是就有了小说《北京折叠》的主人公老刀。”
“以前我写作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达,喜欢什么就写什么。写小说也不特别遵循一般类型小说、通俗小说的一些路数,经常是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写下来。
还有一些小说,是因为生活中遇见哪个人,听到一些故事,让我内心受到触动,以及不能跟其他人讲的一些真实的事,我就改一改写成小说。像《长生塔》那本书就特别明显。《长生塔》甚至是很多心情的寄托,是把一段时间的心情,一段时间听到的事情,转化为自己的一个写作。所以写作更像是我生活中的吃饭、喝水、呼吸一样,通过不断地写作,让我生活得更好。
但是今年,我开始理解大家为什么还是很喜欢类型文学、通俗小说,有点回到了像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看漫画的那个心情,就会觉得,我也可以回归到一个更加通俗小说的写作状态,去塑造一些英雄人物、俊男美女,给读者营造出一个幻境,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经历一段冒险故事。所以今年会有更多为读者写作的部分。”
“在未来科技时代的宇宙探索中,思考领悟中国传统文化”
2016年8月,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世界性科幻大奖“雨果奖”。经过5年沉淀,2021年10月,郝景芳推出科幻新作《宇宙跃迁者》,这是她 “折叠宇宙六部曲” 中的第一部。
“这六部曲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文明是如何产生的,我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大的宇宙背景里面,如果在真实的世界里有无数个宇宙,其实它可能有无数多种文明。”
故事背景设定在2080年。在郝景芳笔下,处于常年战乱的地球文明开始和外星文明协同合作。作品将中华文化融入科幻讲述,通过对秦始皇陵等一系列历史未解之谜的揭秘,开启国风科幻浪潮。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思想和历史真正能放到一个未来科技时代,一个宇宙探索的背景里面,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思考和领悟。”
“我们之前很多科幻作品基本上受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影响,似乎科幻就意味着完全是西方文化。像《星球大战》这样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未来的科技时代,不管是机器人,还是铁甲、宇宙飞船,其实和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的一些作品里面,也有一些人试图把科幻跟中国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但更多的是回到过去,比如回到唐朝或者宋朝,也仍然只是在历史里面融入科幻,中国的元素并不能带入到一个未来的科技时代。
实际上,中国历史传统当中的很多文化思想,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在科技时代,在未来都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做了一些探索,就是重新以精神化的意向去思考古代的一些思想。
我希望用包含中国古典文化的科幻,探索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这很不容易,也不一定能做好,但就是很希望那些激励过我的士人风骨,也能面向下一代宇宙太空。”
直面社会问题,做你能做的事情,带来你能带来的改变
“我曾经做了将近6年的宏观经济研究,对于新闻政策的敏感度是一个习惯。对于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的有解决路径,有的是属于可以缓解可以改善,可以想办法调节,但是还没办法绝对解决。我的态度就是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情,带来那些你能带来的改变。不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些注定可能会有的问题,你就停止行动的脚步。”
“我有一个阶段是真心想做学者。从我2012年上本科,一直到2014年左右刚工作一两年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个世界上最杰出的顶尖学者,梦想发现一个能够影响未来的什么郝景芳定理公式,让后代人说这是她发现的一个重要规律。
但比较受打击的是,我发现自己没那么有天分。面对自己学不会的东西就是学不会,那个时候就特别绝望。这中间也反反复复地摸索,就是看哪个学术方向我真的能够做好。后来我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它不是一个纯学术型的研究机构,更侧重实践导向,就是一方面做一些社会的慈善项目,另一方面做政策研究,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加强改善,包括产业研究、教育政策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地向行动者转变了,即使我没法做一个顶尖Top的研究者,我还可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能够实实在在的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善。”
“当时有很多关于贫困儿童的项目,就是去贫困山村里做家访,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缺什么。大部分孩子压根连山都没下过,村子都没出过,去过最远的地方可能是镇上,父母可能一年回家一两趟这种状态。后来,我创业做童行书院的时候,就想通过现代化的商业手段和科技手段,帮助这些乡村学校和贫困儿童。如今全国几个省市都有我们的支教老师,通过线上线下为乡村学校输入课程,进行教师培训。”
“要让自己从特别黑暗、特别绝望的状态里爬出来,变得坚强”
“我自己觉得,好多事是属于你从觉得特别黑暗、特别绝望的一些状态里面,要是自己能爬出来的话,就会变得坚强好多。不是乐观,而是说再遇到一些其他挫折的事情,大不了还是自己爬出来。”
“我其实是一个挺有死亡焦虑的人,觉得没多少时间好活。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自己不知道哪天出意外就死了,我得赶紧在死之前把我想干的一些事赶紧做了,想去的地方玩了,想写的东西都写了。
后来上了大学,觉得人的寿命很可能就五六十岁,倒推下来,真正能够做事的时间也没有多久,可是但凡任何我想做的事都是没个十年八年做不成的,所以当时就很焦虑,怎么办?时间太少了。
现在其实也会放宽心,感觉科技发展,人的寿命会延长,也可能活到100多岁。但是当年那种心态习惯性的留下来,就这么短的生命,想做的每一件事都这么难,所以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做好两三件事就不错了,我觉得要按这种心态去生活。”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可以有一点长期主义的心态。就是能够真正理解,很多事情但凡是希望它结果好,十年就是一个基本的入门门槛,然后用20年,甚至30年,把它做得精益求精,才真正能够出一些成果,所以心态别急就行了。如果你比较希望出名要趁早,或者说是我要在多少时候登上世界巅峰,这种求之过急的心态未必是好事。我认为,找到你愿意为之付出三五十年不变的事情,这个比较重要。”
令人担忧的思考——认知差异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
“作为世界青年领袖,希望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帮助人们弥补认知上面的很多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又出了另外一本书叫《中国前沿》,主要介绍一些前沿科技。
当代有一个特征,科技发展的速度,其实跑得比人认知发展的速度还快,甚至今天我们说起人工智能,可能和十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可能连上一代发展还没来得及了解,已经有下一代了,就会出现一些人是驱动世界发展的,有一些人是跟着这个世界发展的,另外一些人还没明白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就已经变了。
这个世界每一个时代都会给人带来科技红利,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会带来红利,有人总能赶上红利,有人可能就被落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够把一些世界发展变化的,尤其前沿科技等等,用通俗的方式让大众认知,我们就可能会想到这个世界会往哪个方向转变。”
“我是一个特别能被自然风景治愈的人”
“如果说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我就只干内心充满渴望、最想做的事情。
有时间我会去跑步或者游泳。周末的时候和朋友跳跳舞就特别开心。
我是一个特别能被自然风景治愈的人。昨天在办公楼门口看见银杏叶子变黄了,有太阳光照着,那些烦心事,一瞬间就被治愈了。
以前我最喜欢的干的事情是画画。画画这个东西,它最主要的快乐产生于你几个小时不大动,就在那把画的细节一点一点填上,这个过程特别治愈。现在就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我就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幻想,希望每天还有时间能继续画画。”(记者 苏向东)
【思想者】系列人物访谈
出品人 王晓辉
总监制 薛立胜
制片人 詹海涛
总策划 胡俊峰
策 划 姜壹平 苏向东
编 导 郑 伟
记 者 苏向东
配 音 谢荣宇
摄 制 郑 伟 王肇鹏
后 期 郑 伟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