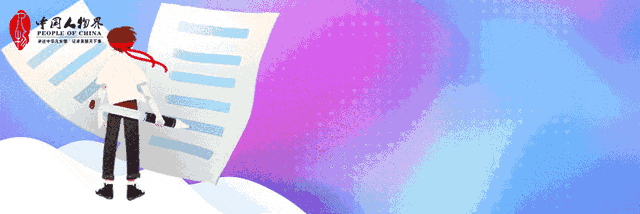丁剑一身黑色西装,端坐台上,注视着台下,眼神真挚,稍显紧张。
今年8月,在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上,因出色的概率论研究获得“2022ICCM数学奖金奖”后,丁剑受邀与数学家丘成桐、杨乐等一同参加一场媒体见面会。
“显然我并不适应这样的场面。”面对数十位记者“围攻”提问,丁剑只有被丘成桐“点名”后,才以寥寥数语回答。
两天后的上午,再见丁剑时,他依然在台上,作为杰出报告人作学术报告。台下既有老资历的数学家,也有年轻俊才,丁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表达流畅自如,举止间自信洋溢。
“80后”数学家丁剑并非不善言辞。他的故事与大多“天赋异禀”数学家的故事并不相似,却能给人以信心与鼓舞。

丁剑在夏威夷。受访者供图
“数学还可以,但与受过竞赛专业
训练的同学比就是个‘渣渣’”
今年1月,丁剑离开美国,全职加入北京大学,被聘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席教授。
丁剑的成长经历并不十分“典型”。
他自小没搞过奥数,没进过数学冬令营,小时候也没有显露出对数学的特别爱好,高考第一志愿也不是数学。中学时期,丁剑只是觉得自己“数学还可以,考试做得快一些,有些兴趣,但与受过竞赛专业训练的同学比就是个‘渣渣’”。
“高中数学联赛是我参加过的唯一的数学竞赛。”丁剑记得,二试有3道大题,只能看懂一道平面几何题,一番苦思冥想,感觉它可以用解析几何做,“我只做了这一道题,思路是对的,拿了这道题的满分,获得省联赛奖项,但名次并不高”。
如今回头看,丁剑坦承,自己对竞赛并没那么在意。“当然进了冬令营的同学比普通学生在数学基础上会有优势,但是再往上,知识储备差得不是很远。”
高考填报志愿时,丁剑与父母所获信息有限,想法也很朴素——将来要有一份好工作。
“凡是新闻媒体上宣传得多的热门专业,我基本都认为是好的。”丁剑笑着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那时最想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但北大的招生老师到他们高中宣讲时劝退了他,“你这个成绩不用考虑了” 。因为他的分数刚过北大录取线,而生命科学是最热门专业之一。
丁剑填的第一志愿是电子,第二是计算机,第三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第四个是“当时看起来前途一般的专业”——数学。
2002年,丁剑“踩着分数线”,被北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录取。
在北大的第一年,很多专业课他学得并不是很理想,只有高等数学他学得最好,但他想去学计算机。
当时有师长告诉丁剑,大意是数学学好了,研究生想念啥都行。他决定“曲线救国”,先转到数学专业,研究生阶段再转学计算机。
数学被誉为自然科学的皇冠、科学的皇后、人类思考中的最高成就……研究数学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更别说“半路转行”。
“乐天”是丁剑身上明显的特点。尽管那时他依然没有做数学研究的决心,印象里“做数学是非常苦的事情”,但他没有因“苦”而却步。
2003年,丁剑准备转系考试时,“非典”疫情来了,北大停了课。
“对我来说,这反倒是一个专注学习、心无旁骛的机会。”丁剑觉得恐慌也无用,就每天拿着高等代数简明教程、数学分析习题集等到教室做题,一遍一遍地做。那时,教室里常常只有一两个人。
后来,一切恢复如旧,丁剑也考入了数学科学学院。作为“插班生”,丁剑还未与同窗建立“革命友谊”,便常常独自去本科生阅览室,从早到晚待在那里。本科生阅览室的人他都很熟悉。
“刚开始有些诚惶诚恐,周围人讨论问题我都听不懂。过了半个学期,一考试我比他们还好一点,自信心就有了。”不过,丁剑知道,“半路”学来的知识没那么扎实,往后还需慢慢补。
始终保持“开门迎客”的状态
和“随波逐流”的心态
在数学科学学院,丁剑遇到了数学生涯中的重要老师——陈大岳。他是随机过程领域的著名数学家、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丁剑用“生猛”描述陈大岳的应用随机过程课堂。“课程之困难十分出名。我担心挂科,真的是拼命学,看了很多课外书,其他课就只是把书上的习题做完而已。”
当时为了学习随机图,他与陈大岳的博士生还开了两个人的讨论班,后来又去中科院“蹭”马志明院士的讨论班。
丁剑没想到,这么难的课,自己真的学进去了,而且还挺感兴趣。大三那年,丁剑与学长爬香山,聊天谈起是否再转学计算机时,他已有所动摇。
有了些许感觉但还未明确方向时,丁剑的状态是导师让他做什么他便做什么。从北大毕业后,丁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师从国际顶尖概率论学者、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Yuval Peres。
随着学习的深入,丁剑越发感受到概率的魅力。“许多方向都有一个人人想解决的大问题或核心问题,但概率的魅力不在于此。它的生命力在于,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踪影,包括纯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等,同时也包括很多应用问题。”
沉迷概率,或许与他的个性有关。丁剑始终有着开放的思维、开门迎客的状态。无论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还是在北大,丁剑的办公室一直开着门,其他人随时可以进去跟他交谈。
“有时他们的问题令我感兴趣或者有些感觉,就开始了合作。我会思考他们的问题需要用到什么概率技巧。”丁剑说。
丁剑喜欢跟人聊天,自嘲为“随波逐流”的心态。在伯克利分校,丁剑结识了Allan Sly、Nike Sun两位好友,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发现了共同的兴趣点。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还是丁剑的英语老师,在聊天中实时纠正丁剑的语言错误。
因为他们合作完成的random k-SAT问题,以及此前与合作者在马氏链和随机游动覆盖时方面的研究工作,丁剑获得了“戴维逊奖”。这是洛勒·戴维逊基金会为奖励从事概率论研究并取得卓越成绩的青年数学家而设立的奖项。丁剑是第四位摘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这样聊天聊出来的好友、研究兴趣和成果,不止一个。
“博士期间,我一直是跟导师合作,接下来几年,我发现我好像能跟很多人讨论,做很多不同的方向,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毕业以后有长进。”丁剑说。
数学家解决问题通常要以年计,丁剑也有焦虑、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做不出来是常态。难的事情太多了,最难的是,一点想法都没有,连错误的想法都没有。
这时,丁剑会跟师兄弟一起吃饭、吐槽,一个人时也听听音乐,主要是罗大佑、李宗盛、邓丽君、王菲等的老歌,此外每天至少保持两个小时专注思考。
丁剑说,持之以恒地思考才最重要,“哪怕自我怀疑,我也不曾停下脚步”。
希望“我艰难前进的样子”
能鼓舞“自我怀疑的年轻人”
丁剑回国前的“最后一站”,是受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Gilbert Helman讲席教授、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教授。
他每天早上9点从住所出发,步行大约25分钟到达办公室,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放松和思考的过程。
一路植被茂密、绿草如茵,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在大脑中安排一天的工作。
在宾大,他在随机几何、刘维尔量子引力、统计物理模型等概率论与统计物理的交叉方向、基于统计应用的理论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丁剑说,回国这件事情一直有打算,并不突然。出国15年,丁剑从未中断与国内的联系,也一直与北大的老师有合作。
文化认同感是驱动丁剑回国的重要因素。“我知道‘东邪西毒’,但听不懂他们聊的‘比特斯’(一支英国乐队),在国内跟人说话、聊天,更加如鱼得水。”对丁剑来说,这无关语言,事关文化。
回到北大,丁剑考虑,不光要冲击那些最难、最有挑战的问题,也要开始在这片土壤上布局学生培养。
过去大半年,丁剑在做“有意义的铺垫”,他选择了尚存潜力的方向,即组合概率和组合统计。“我认为它能够通向更宏大的课题,即随机优化问题的计算复杂性。同时以我们的水平,能够在几个月内取得进展,把学生的士气调动起来,让学生能够学到相关知识,接受一些基本的研究训练。”
近年来,为了锻炼身体,丁剑开始跑步,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00天跑步,每天4~5公里,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
如今,年轻一代的数学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学术环境。在他们面前,既有最好的条件,也“埋伏”着太多学术外的诱惑和难题,需要“找到自己的路”。
丁剑认为,博士毕业后的那几年很关键。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博士毕业后,不应完全围绕着博士期间的工作去做,因为博士论文题目很难是你自己的课题,但也不能另起炉灶。
“如何把博士期间熟悉的方法、技巧、思维,应用于另一个合适的场景,提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很重要。”丁剑说,这也是尊重学术界游戏规则的表现,“拿到Tenure(职位)之前必须接受考核、拿出一些证据,证明你的独立性、原创性,接下来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
丁剑不希望数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总因辛酸凄惨的奋斗故事而被人熟知。
数学家也是普通人,拥有平凡的生活,在追寻学术荣誉的道路上有奋斗更有所得。
正如丁剑在获得“2022ICCM数学奖金奖”发表感言时所说的,“在以后士气低落的日子里,看一眼这个奖牌能够振奋一下精神,又或者其他自我怀疑的年轻人,见到我在数学道路上艰难前进的样子后,而生出一种‘连他也可以,我一定也行’的豪气,这枚奖牌就实现了它最大的价值”。
《中国科学报》记者 韩扬眉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