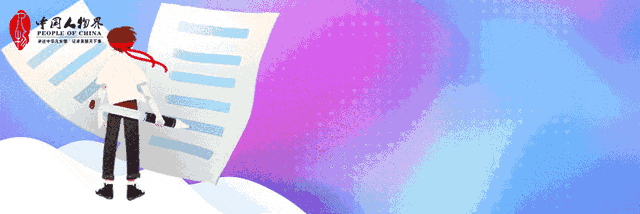那辆白色面包车一出发,村民们就知道,村医邓前堆又要去怒江西岸问诊了。
沿着环山的公路,开上几百米,邓前堆就来到了“连心桥”。桥狭长逼仄,宽仅4.5米,只允许单车通行。取道于此,不出10秒,邓前堆就能跨越奔涌的怒江。
2公里外,两条细长的溜索悬在江上,那是邓前堆的“老搭档”。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6个小组被百米宽的怒江切分为二,村卫生室在江东岸。当了39年乡村医生,前28年,邓前堆每逢去江西岸问诊,只能绑上绳索,握住滑轮,顺着溜索过江,每次都提心吊胆。
2009年,溜索过江的画面被媒体捕捉,邓前堆成了家喻户晓的“索道医生”。节目最后,邓前堆许下两个心愿,“第一,建一座能通村的桥;第二,每个村小组能修通公路。”
2011年,“连心桥”与另一座“幸福桥”竣工;水泥路也一寸一寸爬上了山,至2020年,最远的村小组也通了路,去年,路边的防护栏也建成了。顺畅的交通让贫穷的村庄有了“奔头”——村民不再种植只做裹腹之用的玉米,转而种起了售卖价格昂贵的草果;摩托车、小轿车与大货车涌入村里,将草果运往他乡,换回粮食与财富。
邓前堆的愿望,一个一个实现了。

横跨怒江的溜索,如今已成为拉马底村的一个标志。受访者供图
溜索上的前半生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1982年,拉马底村村医友尚叶在给19岁的邓前堆治好了痢疾后,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
那是青年邓前堆第一次生病,对他来说,友尚叶就像是他的救命稻草。时年25岁的友尚叶是村里唯一的医生,被村民叫作“老医生”。当时,他正好想再找一名医生搭班,看中了邓前堆的初中学历。
邓前堆答应了。他想,“我也可以成为村民的依靠。”
跟着友尚叶学了一个星期,把药品名称记住后,邓前堆又去乡卫生院学习了一年,正式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一个月工资25块钱。两三年后,友尚叶当了村支书,村医只剩下邓前堆一人。
在石月亮乡,拉马底村是唯一被怒江切割的村庄。6个小组1000多名村民散居在近50度的陡山上,被百米宽的怒江分成东西两岸。邓前堆不仅要负责江东3个小组,还要负责江西岸高黎贡山上的3个小组。两条细长的溜索横亘在江水上方30米,一头高,一头低,绑上绳子,握住滑轮,顺溜下去,约一分钟就到了对岸,要是走山路,得翻山越岭,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
溜索是拉马底村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从邓前堆小时候起,这两条溜索就悬在怒江上空了,每三年更换一次。怒江水流湍急,声如擂鼓,一旦掉下去,几无生还可能。至2012年建桥为止,掉下溜索的有8人,5人找到了尸体,至今仍有3人失踪。

邓前堆出诊给高血压患者测量血压。受访者供图
两岁以下的小孩不准过江,一旦生病,邓前堆就得过溜索出诊。一开始,他背着15斤重的医药箱,被家属带着过江,短短60秒的时间,他不敢睁开眼睛,脑子里塞满了掉下江的场面,等到了对岸,邓前堆已经“呆住了”,家属喊了两遍放手,他才回过神来。
为了不麻烦村民来回带他,邓前堆开始自学溜索,却怎么也学不会“刹车”,愣是直直地冲下去。有一天晚上9点,天下着雨,江西岸来了个人,叫邓前堆赶紧过去。夜色浓黑,他顺着溜索滑向对岸,什么都看不清,迎头撞上了溜索末端的石块,药箱里的注射剂被撞碎,他左腿膝盖至今留着一条浅浅的伤疤。
后来,他学到了如何“刹车”——手里捏一把稻草,需要停的时候,就用它握住溜索。病人的呼救总是不定时而来,邓前堆成了溜索最频繁的过客,最多时一天能过两三回。他还在拉马底村举行的“溜索比赛”中,以39秒的成绩拿到过“溜索大王”的称号。
很多年里,邓前堆是拉马底村唯一的医生。他也想物色搭档,然而,对年轻人来说,乡村医生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有一点知识”的年轻人渐渐都往外走,去省会昆明打工。看病时,邓前堆总能听到老人吹嘘,“钱如流水一般从外地汇过来,一个月几千块钱。”
当时,邓前堆正值壮年,乡村医生的月工资涨到了一百元左右,村里人劝他,妻子也催促他,去外地打工吧。
“答应了就不能反悔。”答应做村医时,老医生友尚叶的这一句话,被邓前堆当作了一个承诺。
被看见的村医
个子不高,身穿白大褂,背一只皮质医药箱,熟稔地套索套、过溜索,步伐矫健地爬上陡峭山路。
这是邓前堆留给公众的第一印象。2009年,有媒体跟拍采访他,节目播出后,邓前堆成了家喻户晓的“索道医生”。
节目最后,记者问他,你有什么愿望?思考了五分钟后,邓前堆说:“我的第一个愿望是,建一座能通村的桥,这对村民和我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修了桥之后,每一个小组都能修通公路,让村民从家门口就可以坐车。”
两三个月后,他收到一条中央文明办的短信,上面写道,“你的愿望要实现了。”
不到一年,桥开始建起来,路也开始修起来。2011年,两座桥竣工。一座被命名为“连心桥”,寓意怒江东西两岸不再分隔;一座被命名为“幸福桥”,寓意“过江不再害怕”。

横跨怒江的“连心桥”。受访者供图
邓前堆让乡村医生这个群体被越来越多人看见,他也成了村医们的“代言人”。很多乡村医生写信给他,希望邓前堆能替他们诉说困境。
苏唐文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新南村的乡村医生,当年快要退休的他,在给邓前堆的信里,写下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乡村医生没有退休机制,我们养老也没有盼头。”
他是新南村第一个乡村医生,高中毕业后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农村,被选拔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在此之前,乡村医疗还未普及,许多传染病流行,不少村民患病还信神医巫婆。
至2003年,全国乡村医生超过79万,经过不断的培训进修和自学,他们扎根在乡村,己经大大改变了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然而,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晰的职能岗位,待遇也各地不一。那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颁发,苏唐文第一次觉得这个群体被国家重视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媒体、人大代表,希望能把乡村医生的待遇提上去。
如苏唐文一样找到邓前堆的乡村医生遍布12个省共100多人。邓前堆意识到,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十八大党代表,应该为这个群体发声——完善农村卫生室的用房建设、留住艰苦地区的医疗人才、完善乡村医生退休待遇……无论开会还是接受采访,邓前堆一直都在为改善农村医疗提建议。
2013年8月,原国家卫计委发文要求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建立乡村医生到龄退出机制。去年,72岁的苏唐文从乡村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每个月能领到600多元的退休补助,“工资”反而比当医生时还要高。
村民的“救护车”
早上9点,吃过两碗米饭后,邓前堆穿上白大褂,开始坐诊。如今,村卫生室有六间房:邓前堆坐在药房问诊,右手边数过去是诊断室、观察室,左手边是治疗室、材料室、公共服务室。药品和仪器也源源不断地加入卫生室——电脑、血糖仪、血压表,还有一台站上去就能读出身高体重的测量仪。
村民喜欢早上来看病,下午看病的人少了,邓前堆就开车出诊,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回家后,他才会开始吃第二顿饭。
一天两顿饭,是贫困烙在邓前堆身上的一个印迹。
拉马底村树木郁葱,山地阴凉,土质松软。以前,村里种植的都是玉米、土豆等农作物,每年5月播种,10月收割。中间的5个月,村民总是为裹腹发愁。邓前堆从小便知道,每一顿饭都是挣来的。“今天吃得饱饱的,明天就不知道吃什么了。”
饥饿的时候,野菜、菌菇,能扒拉到什么就吃什么。削减了午餐,吃的也不干净,肠胃炎是拉马底村人常得的慢性病。
建桥修路后,一种名为“草果”的种植物被引入拉马底村。草果喜阴,一般栽培于疏林之下,种植2年开始结果,加工后可做香料,收购价约4元一斤,比玉米高了七八倍。2011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钱,如今,可到三四万元。
村里开始热闹起来。最为显著的是交通工具——摩托车、拖拉机、大货车、小轿车……安静的拉马底村渐渐拥有了“噪音”。
来往的车流中,一辆白色面包车作用最为特殊。它是邓前堆的出诊车,也是拉马底村的“救护车”。有村里医治不了的村民,邓前堆就会把他们送到乡医院、县医院去,一送就是一天。
2012年一次公益活动,邓前堆获赠了一辆面包车。为了能将车开上新建的公路,49岁的他开始学考驾照。那是邓前堆第一次接触电脑和汽车,他学了7个月,是驾校里学习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以往崎岖的山路,一走就要四五个小时。现在,邓前堆能一直开到病人家门口,时间缩短到三四十分钟。2019年,用了7年的旧车报废,他又买了一辆新面包车。
一个月前,怒江西岸一位65岁的村民薅草时不慎戳到了左眼。邓前堆出诊时,已是四五天后,村民眼球充血,眼睛发肿,泪止不住地流,在哀哀呼痛。
村卫生室没有眼科检查设备,邓前堆将他接上车,送往50公里外的乡医院检查。没想到,乡医院也无法处理,他又开车到170公里外的县医院。在医院里,邓前堆就是村民的陪诊员,替村民排队、挂号,有时村民急着回去种地,他还得劝解住让他们安心治病。
自早上8点开车出诊,返回拉马底村已过了下午6点。邓前堆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老去的人,老去的村庄
42岁的村民普先生一家三代人都是邓前堆的病人。
他70岁的老父亲是拉马底村47例高血压患者之一,视力不好,轻易不会出门,每次感到头晕眼花,总是一个电话把邓前堆叫来。普先生经常头痛,查不明原因,每次去看病,邓前堆都会多叮嘱几句注意事项。2岁的小儿子生下来就身体不好,一有发烧感冒,还是会找邓前堆。
“他基本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习惯了他给我们看病。”普先生说。
从医39年来,邓前堆走遍了拉马底村每一个角落,清楚每一户人口的生育与死亡。从一个孕产妇怀孕、生产,跟踪到新生儿6岁为止,他甚至比每半年统计一次人数的村委会更清楚村里人口的动态。

邓前堆在村卫生室给患者看病。受访者供图
看着自己的村庄富起来,医疗卫生条件也越来越好,对58岁的老村医邓前堆来说,“已经没有了遗憾”。唯一让他担忧的,是自己“老了”。
四五年前,他发现自己看不清药品的名称,也看不清患者的伤口。输液时,他架上了200度的老花镜,不敢再给病人缝合伤口。去下乡宣传,第二天他总感觉力不从心。之后,高血压也找上了他。
2017年,电脑搬进了拉马底村卫生室,开始信息化管理村民的病历。邓前堆学得吃力,逐渐将医务交给了另一位村医恰付英。
恰付英今年45岁,2005年开始做村医,是邓前堆找的第5个人。她是石月亮乡利沙底村人,18岁嫁到拉马底村。母亲患有支气管炎,丈夫身体也不好,她就想学医照顾家人。
经乡卫生院培训后,恰付英成为邓前堆的搭档。刚当上医生不久,她连打针都害怕,鸡毛蒜皮都得问邓前堆,怎么诊断,如何配药,他都会一一细心回答。入户打疫苗的时候,邓前堆从不让她背医药箱。
现在,恰付英包揽了6岁以下儿童打疫苗、饮用水卫生检查等工作,邓前堆只用负责慢性病人随访工作。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高血压、高血糖患者占村人口比例逐渐超标,他们是邓前堆的重点关注对象。
今年9月开始,邓前堆有了一个新身份——“家庭医生”,针对那些不方便到村卫生室就诊的婴幼儿、妇女和老年人展开定期的家庭随访。
和以前相比,乡村医生的待遇提高了。邓前堆现在每月能领1200块钱,按照多劳多得的方式,恰付英每月能有三四千元。但是,这份职业对年轻人仍旧没有吸引力。
交通便利后,拉马底村也成为了一个“候鸟”村。每年二三月份,年轻人外出打工,年底再全部“飞”回来。邓前堆总是发愁,要用什么留住年轻人。
邓前堆听说,拉马底村隔壁的村子,一名老医生离岗了,乡卫生院想再招一名村医,整整招了三年,仍旧没有音讯。去年,72岁的苏唐文退休,新南村也没有了乡村医生,一些熟悉的邻居,还是会找苏唐文看病。
和村庄一同老去的邓前堆与恰付英都没想过离开。“我想工作到被通知离岗的那一天。”邓前堆说。
(新京报记者 徐巧丽)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