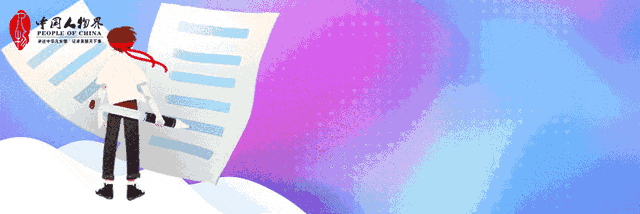编者按
医者,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学进步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无数璀璨的明珠,他们为护佑生命而战,为现代医学开疆拓土,留下了数不尽的济世良策。为抢救性记录国之大医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和卓越贡献,光明日报今起推出各大医院老专家、老教授口述史专栏,以高度浓缩的笔触,深切展现他们一生与党同行,用热血与求知铺就革命、救治、建设之路的感人瞬间,彰显大医精诚的大家风范和高贵品格。
9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迎来百年华诞,我们首批推出协和老专家口述短文。协和人常说,协和的大夫是“熏”出来的,作为中国现代医学的肇始之地,他们的个人记忆也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佐证。

1930年2月出生,著名神经内科学专家。从事神经病学研究60余年,在肌电图、神经电图及脑诱发电位等方面开展大量工作,在国内最早开展了运动障碍的肉毒毒素治疗。1992年“肌电图及神经电图在神经肌肉病中的应用”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1984年牵头成立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肌电图与临床神经电生理学组并任组长。曾任国际临床神经生理联盟执行委员。
聚光灯下,讲述徐徐展开,九旬铅华写满了她对祖国的赤诚至爱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
——访谈人傅谭娉
大学时,我最初上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因为喜欢外文,之前也学了很多。后来有一次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讲座,讲苏联的医疗体系怎么服务人民,我一下就被吸引了,就想读医学院。学校同意我参加一个考试,考过了以后,我就转到医预科,1951年8月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的张孝骞、林巧稚这些老教授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他们教得是真好。冯应琨教授在我们临床实习的时候,让我们跟他一起做一项肝豆状核变性病人的钙磷代谢研究。我们每天晚上做完功课以后,就去做实验室研究。后来我们一起发表了文章。这让我认识到,协和医院的医生都不只是做临床,还必须要做科研,这点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1978年,我通过了首批留学生出国考试。冯应琨大夫马上查资料,知道全世界最好的肌电图专家Buchthal教授当时在丹麦皇家医院工作。他给我写推荐信,Buchthal教授同意我去学习。第二年的时候,Buchthal教授邀请我跟他一起做一项神经病理的研究论文。我拒绝了他,我说:“我想专心学神经生理。”他又问我:“你真的不想学吗?你要是写了这篇文章,还可以把名字署上去,那你就会有很大的声誉。”我说:“我无所谓,我回到协和,还是做一个普通的神经科大夫,研究肌电图的工作。”很多人觉得外面生活好。我是在香港待过的,英国人怎么对你的?我早知道了!那种日子我不愿意过,哪怕当时条件差一点儿,我也要做自己的主人。中国需要人,需要有学问的人,我想为祖国服务,我是一定要在中国的!
1981年8月,我进修期满就迫不及待地回国,开展了实验室改革,对协和肌电图室的工作进行了知识和仪器的更新,改成像国外一样的要求。1984年,我们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成立肌电图与临床神经电生理学组,我、301医院的沈定国、北医三院的康德瑄、上海中山医院的王遂仁一起牵头全国神经生理的工作,在全国推广肌电图。通过学会,我们把全国搞神经生理的人都请来,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学术年会。其中最盛大的是1996年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亚洲临床神经生理学术会议,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典、比利时、丹麦、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来了14位专家、200多位代表,加上中国的代表,有1000多人参会。
当时在英国的学习班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全身性肌张力障碍性的病人,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国外用肉毒毒素治疗这种病,有效果。比如说歪颈,给这边收缩的肌肉打肉毒毒素,肌肉松弛了,病人的头就正过来了。我在国外发现了这个新的治疗方法,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药。1992年,我联系到生产肉毒毒素的美国公司。他们让香港子公司的人到北京来,和我们一起做。协和开设了肌张力障碍疾病专科门诊,治疗了大约30例病人。很快我们又听说,中国兰州有位王荫椿教授,他在美国学习了肉毒毒素的生产,现在中国能自己生产肉毒毒素了,而且改良了方法,不用血清,更安全。我们就一起合作,比较中外产品效果,结论是不相上下,都很有效。
做医生,是我自己选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我这一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国家派我到国外,跟着最好的神经生理学教授学习,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向全国神经生理领域的人传播,我感到愉快、荣幸!协和不只是看病,还重视研究,医疗、教学、科研都要搞好。因为这三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注意这三点,医院水平就会越来越高。协和的老教授都是特别好的大夫,一辈子就是想做一个医生、做研究、教学生,想法很简单。对病人好,对病人认真,这些协和的老传统,要坚持下去。
(光明日报记者崔兴毅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 05版)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