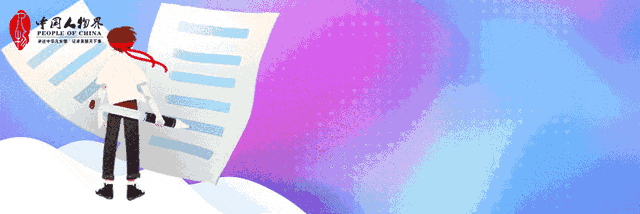1月2日,著名翻译家、学者王智量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94岁。
喜欢普希金的读者很难错过王智量翻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尽管《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本众多,但只有他的译本按照原文原有韵律来译。1999年,在普希金诞生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俄驻华大使特别感谢了王智量,因为他原汁原味地翻译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
王智量一生从事俄语、英语翻译,旁涉法、德、日文,还译有《我们共同的朋友》《贵族之家》《前夜》《帕拉莎》《安娜·卡列宁娜》《死者》等30多部文学经典。2019年11月,92岁高龄的王智量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翻译之外,他亦有很高的学术与文学成就,写有文学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海市蜃楼墨尔本》,散文《人海漂浮散记》《往事与怀念》,主编《外国文学史纲》《俄国文学与中国》等。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8册《智量文集》,共计500多万字。
在作家李洱心里,智量先生是真性情的大才子,大翻译家,真学问家;在作家陈丹燕的回忆中,智量先生是一个非常抒情的老师,他被很多学生喜欢和崇拜。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从他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缘分开始回顾他的大半生,以此纪念一位能够同时熟练翻译俄文和英文的翻译大家,一位在命运沉浮中向上而生的知识分子,一位炙热的、诗意的可爱老人。

2016年,在医院的王智量。丁晓文 摄
(一)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诸多译本中,王智量的译本堪称经典,俄罗斯如今所有的普希金纪念馆都陈列着他的译本。
一切或许可以从1949年说起。
他和同学们被送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不想在秋林公司看到了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原版书。当时这样的书实在稀有,他把它捧在手上反复翻看。尽管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但他如饥似渴,欣喜若狂。因为没有钱,他转身就把从上海带到北大去的一件西服上身拿到店里卖掉,换来了这把打开俄语翻译之门的珍贵的钥匙。

王智量人生中的第一本俄语原文《叶甫盖尼·奥涅金》
晚年在《朗读者》节目里回忆起来,他说:“当时自己还不懂他是什么名家,只觉得这部作品里面所描写的人物那么纯洁,那么真诚,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等到他读俄语二年级的时候,他把《叶甫盖尼·奥涅金》从头到尾都背了。
一共400多个十四行诗节,他每一个都会背。
(二)
大学毕业后,王智量先在北大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也曾以托尔斯泰研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他受翻译家余振启发,开始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余振先生特别教他,译诗要译得像诗,要注意原诗的韵,而俄语诗的韵跟中国诗的韵不同。译诗既要保留原诗的形式,也要有中国诗的特点。随后他花了两个月翻出十个十四行诗节,其中第八章的第四十六首诗曾被何其芳先生引用于名作《论红楼梦》中,发在《人民日报》上。这对王智量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但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并被发配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改造,学术研究戛然而止。
在西柏坡村,《叶甫盖尼·奥涅金》依然是他生活里的一束光。他把这本书的原文带上,反复读,有机会在脑子里想到的就把它翻译出来,“把菜种撒在地里,这一行撒过种子的上面铺一层土,然后拿脚把土踩实在。我一面在那儿踩,心里一面就想诗的韵律。这样一天下来,我劳动也不累,这一节诗就翻译得很好。”
那时还很难买到纸,他就把报纸边上那一条白的没有字的部分都撕下来,也常去捡别人丢掉的香烟盒,晚上在那些“废纸”上写下白天想到的文字。几年后到上海,他哥哥一看行李就发现了一个口袋,那个口袋里全是报纸边,还有上海人叫“乌草纸”的东西。
“文革”时期,《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初稿已经出来了,王智量把它们放进书橱里。他担心手稿被造反派毁坏,就在书橱上贴了两句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这话就说:“你这是骂谁,是不是骂我们毛主席?”他赶紧拿过《毛泽东选集》,翻出其中的一句话:“我奉劝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把这句话写出来贴在墙上。”就这样,躲过一劫。
对于这段经历,后来在接受华师大档案馆口述记录时,他说:“现在我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们这一辈人听,也许能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没在那个时期死去。”
(三)
1978年,王智量结束了他在向明中学的漂泊任教,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他等来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他的学生们几乎都难以忘记他教《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的场景。1981年,作家陈丹燕坐在大教室的第二排,看到王智量说起普希金的长诗,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大雪中跟着流放的丈夫前往西伯利亚时,眼睛里闪烁的泪光。“因为老师的泪光,我们这些女生,会在三十年以后,在老师的生辰庆祝会上,争相朗读达吉亚娜的信。也许我们班上的女生,一生都不会忘记老师教过的这首俄罗斯的长诗。”
1982年,历时二十余载,王智量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成为“中国尝试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第一次让中国读者原汁原味地领略了“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
他百感交集,最大的遗憾是曾给他极大支持的母亲没有等到这本译著的面世。后来他把书拿到母亲坟上,烧给她,告诉她:“这本书印出来了。”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外,1980年代他还翻译了《我们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等,推出学术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主编《外国文学史纲》。1980年代末,他涉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的民族接受”,并受邀参加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比较文学大会。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主编了《比较文学300篇》和《俄国文学与中国》。
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

王智量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四)
1990年代,除了翻译《贝壳》《上尉的女儿》《安娜·卡列尼娜》《前夜》《贵族之家》《屠格涅夫散文诗选》等大量作品,王智量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
这是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就的小说,写上世纪中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个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北边远地区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所闻。

《饥饿的山村》
小说刚出版那阵,作家李洱与格非正好去过他家里。王智量和他们说起有几个译者要翻译《饥饿的山村》,还开玩笑:“获诺奖需要五个语种的译本,现在还差一个。”那时候独联体刚成立,王智量还喜欢说家庭就是个独联体,李洱与格非听了又是大笑。
“让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看过很多先锋小说,对先锋小说有很深的理解。有一次,我与格非从他家出来,还对此感慨不已。”在李洱看来,智量先生的艺术感悟力,在大学教授中肯定是顶尖的。
前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经典译作网格本丛书的发布会,现场也播放了王智量的采访视频。李洱一直对那个画面印象深刻:“他的面孔离镜头很近,我一看就知道,他的客厅还是那么小,书都堆满了。他鹤发童颜,双目奇亮,在镜头前反应极快。”
“奥登说,诗人是持续成熟到老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在成熟,所以他总是不停地修改译本。”李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智量先生的俄语、英语翻译,毫无疑问,都是文学瑰宝。他的逝世,是文学翻译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而且不可弥补。”

(五)
去过王智量家里的人很难不注意到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屠格涅夫散文中的一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这句话,仿佛也是王智量的人生写照。
“我喜欢诗,但我自己不会写,所以才喜欢翻译,用别人的灵感来抒发感情。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它在替我说话。”王智量曾说,“翻译既是我苦难的源头,也是我生活下去的力量,最终引领我走向通往幸福的道路。”
他喜欢屠格涅夫,尤其是屠格涅夫老年时期的《散文诗》。他觉得这本书应该叫作《孤独集》——写出了一个孤独老人的内心世界,而且把人性中最淳朴、最珍贵的东西展示了出来,“他写一只小麻雀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一只狗扑过去咬它,这时老麻雀不顾一切地扑下来救小麻雀。两者力量的差距那么悬殊,老麻雀却敢于扑向大狗,这是多么伟大的爱?他的作品令我感同身受。”
坚强和爱,是陈丹燕对王智量的一大印象。“他说过,任何个人的灾难岁月,如果不能摧毁这个人,就会给这个人的经历带来非常正面和坚强的元素。就好像他的‘右派’岁月,最后教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而且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
陈丹燕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听闻老师逝世,她脑海中闪过了好些画面:他的俄语课堂,他教她英文精读,他告诉她一段翻译中的危险和精妙各在哪里,他为她和陈保平的《去北地,再去北地》写序……她还忍不住哼起老师教她的罗伯特·彭斯经典诗歌——《A Red Red Rose》。

2016年5月,陈丹燕去医院看望王智量。 丁晓文 摄
那么,在这个冬天,我们也为王智量先生献上一枝红玫瑰,并以他译乔伊斯《死者》的结尾来做这篇纪念的句点吧: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罗昕)

王智量 丁晓文 摄

 PC版本
PC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