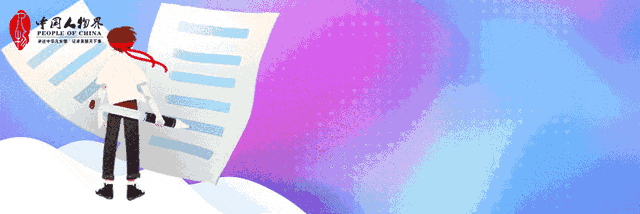在上海大剧院看《惊梦》的世界首演,又一次体会到16年前看戏“惊为天人”的感觉,那次是看《阳台》——把欧洲的编剧法(farce笑剧)和当代中国农民工的人物故事结合得天衣无缝。那时我还完全不认识影视明星陈佩斯,《阳台》让我恍悟他还是如此杰出的剧作家和导演。现在我跟他已经很熟了,指导博士生全面深入研究他的《阳台》和《戏台》,写了一本极有特色的博士论文;因此他这次的《惊梦》着实有点惊到了我——这部全新的戏(也是《戏台》编剧毓钺写的)竟比《阳台》《戏台》又高出了一大截!全剧三四条故事线融为一体,喜剧悲剧正剧浑然天成,编导演舞美全都炉火纯青,看不出一丝“舶来品”的痕迹。

一个更大的惊喜是,在这部“戏中戏”里,还看到了《白毛女》的“喜剧化处理”。记得在我主持的一次讲座上,佩斯说艺术家喜剧的眼睛可以把一切都看成喜剧,包括《哈姆雷特》等最著名的悲剧,还如数家珍地甩出一连串“点悲成喜”的点子。我在一旁故意用他父亲陈强老先生最著名的作品来“将他一军”:那你父亲演的《白毛女》呢?是不是也能看成或者做成“喜剧”?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说:《白毛女》?太喜剧啦!杨白劳、喜儿、黄世仁都可以是喜剧人物呀!杨白劳不是卖豆腐吗……他嘴里立马就蹦出好几个喜剧段子,让挤满了剧场的听众笑得几乎要掀翻屋顶。当时我以为,他也就过过嘴瘾,《白毛女》不可能真的在舞台上变成喜剧。谁想十几年后,他这部《惊梦》里还真出现了一个笑点不断的“白毛女”。昆曲戏班和春社本来只会演《牡丹亭》等传统老戏,应了解放军的盛情邀约,立马就要赶鸭子上架演现代戏,可该怎么演呢?喜儿穿青衣的珠翠行头念“苦——啊——”?大春“得胜回朝”,像将军那样扎靠插旗?台上的角儿左右为难哭笑不得,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当然,演员最后还是穿上了宣传科长送来的朴素“时装”。演戏时战士们的反应火爆之极,叫好声一浪又一浪,陈佩斯演的黄世仁还被打了一枪——其实并没打中,但他还是吓得拼命在长袍上找枪眼。解放军首长赶来安慰他,说当年在延安看《白毛女》,演黄世仁的陈强也差点挨了枪子——哎!你长得跟他是不是有点像呀?酷似其父的陈佩斯瞪着眼装傻,貌似不懂他在说啥,让大剧院的观众笑岔了气——大家都知道,刚刚下场的陈强孙子陈大愚也在侧幕后面大乐呢。
这个《白毛女》还有一层更深沉的喜剧效果,更是完全始料未及。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官跟解放军首长当年在黄埔军校同过学,恰巧也是和春社的戏迷,他俩还曾一起票过昆曲,唱过《牡丹亭》。他的副官得知后投其所好,逼着戏班也要演个戏劳军,却因对昆曲一窍不通,答应他们就演那最能“提振军心”的《白毛女》。演出中途又响起了枪声,这次却是兴师问罪的军官打的——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被戏班“戏耍”了!毓钺和陈佩斯只字未改《白毛女》的剧本和人物,只是巧妙地将其“再语境化”,这个喜剧性的重构不但没对原著有丝毫的轻慢,反而加倍有力地证明,《白毛女》这部红色经典有着多么神奇的魅力!
《惊梦》是个十分奇特的戏中戏——既垫着最经典最永恒的《牡丹亭》,又托出了最有时代性的《白毛女》;三出戏都悲喜交融,又分属完全不同的类型,恰好都能代表“中国戏剧之最”。这台戏乍一看有点像“梅兰芳+《茶馆》”,但绝不是简单的加法;《惊梦》把话剧、戏曲及其诸多社会价值化而为一,疫情之后真应该去国际舞台上好好“显摆”一下——最好是和《牡丹亭》《白毛女》一起去。
我的“二刷”是和国际剧协总干事托比亚斯·比昂科内一起看的,他也大为赞赏。《惊梦》情节线多,故事比较复杂,现场的低声翻译只能抓大放小,不料他竟对我没顾上翻译的一些配角如解放军宣传科长(东斗饰)的表演也很欣赏——这位看戏“老法师”对演员动作表情的洞察力也给了我一个惊喜。谢幕后我们一起去后台见艺术家,祝贺演出成功。他告诉陈佩斯父子,十分期待《惊梦》的国际巡演。
(原标题:剧场手记 《惊梦》的惊喜)

 PC版本
PC版本